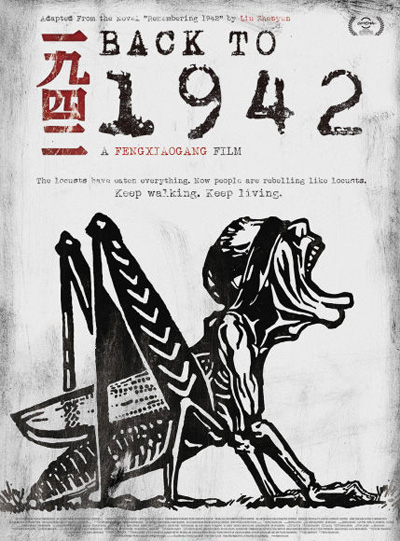
在經歷了一場餓殍遍野的大饑荒和一次慘絕人寰的大逃荒之后,張國立扮演的“老東家”決定不再往前走了,所有的親人、朋友死的死、逃的逃,活著本身都變成了一件因孤獨而意義待考的事,那就回家吧,死,也死在家里。于是,老東家逆著逃荒的人流走去,并收留了一個在路邊痛哭的小女孩。許多年后,這位小女孩的后代中出現了這個故事的講述者。
從結局來看,《一九四二》無疑是一出冰冷徹骨的悲劇,三千萬逃荒的災民,一路流亡而去,因戰爭、疾病、寒冷和饑餓漸次凋敝,直到最后他們也沒有得救,對于活下來的災民來說,體面、尊嚴甚至民族大義都變得空前猶疑,在這場生存大戰中,沒有贏家,只有苦熬過來的幸存者。
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節”,飯都吃不飽,一切都會在饑餓中變得輕飄飄。性、身體乃至人身自由都成了待價而沽換取糧食的工具,禮義廉恥所構筑的傳統價值觀在空前的饑餓中變得薄如蟬翼,不僅傳統的儒家宗法理念被棄若敝履,就連基本的家庭倫理也餓得頭昏眼花、不堪一擊——丈夫出賣妻子,父親兜售兒女,以及各種通奸匪劫事件,更是不一而足。雖有原作的堅實基礎,但在影片拍攝前,導演馮小剛還是多次前往實地調查搜集史料,無奈史實太駭人,在我們這個沒有分級制的電影市場里,導演只好大量舍棄過于“刺激”的素材,并大幅弱化了電影中種種因饑餓而導致的道德、倫理沖擊(當然也考慮到了普通觀眾的接受度),不過即使這樣,當我們在電影院里看到《一九四二》時,其震撼程度也是近年來的國產片無法比擬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在他的大饑荒研究中指出,導致全面性大饑荒的原因往往并不是糧食總供給量的不足,而是由于信息封鎖、分配不公等個人權利的“貧困”所致。天災人禍,天災在前頭,可壓倒駱駝的最后那根稻草,還是人禍。1942,水旱蝗湯,河南老鄉始終沒忘加上那個“湯”。《一九四二》的電影基本上分為兩條大線索,一條是老東家等人的逃荒,另一條就是國民政府應對饑荒的措施。當然,日本侵略軍給救災造成了不言而喻的困難,但國民政府在饑荒時依然貪污腐化、橫征暴斂,軍隊甚至不顧客觀困難對災民強征軍糧,凡此種種,相互疊加,終于釀成了這場災難。要不是美國記者白修德如實報道這場饑荒,通過美國政府給蔣介石施加了壓力,恐怕蔣還遲遲不會開倉放糧(電影中也呈現了這條故事線)。總的來看,《一九四二》基本客觀的還原了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對于災民的罔顧——就算有李培基的殫精竭慮,但大的政治環境腐壞了,個把清官根本無法扭轉局面。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多災多難的歷史,民族存亡的巨大危機始終讓“救亡壓倒啟蒙”,于是,人道主義的災難往往被掩蓋或扭曲了,在外敵入侵的關頭,一切以抵御侵略者為重。但是,吃飯的問題不解決,怎么解決其他問題?《一九四二》也呈現了日本侵略軍用軍糧賑濟災民的史實,當然筆墨并不多,對于日軍的暴虐行徑,影片也忙不迭的進行了交待——日本鬼子給了災民救命的白饃,但接下來就是不由分說的濫殺。很顯然,《一九四二》的深處隱藏著一個民族主義和人道主義相沖突的主題,導演在處理這一敏感主題時,不得不小心翼翼。應當說,影片現在所呈現的面貌,既符合大的歷史事實,也不會在立場上授人以柄。
有史料記載,由于國軍和日軍在對待賑災態度上的迥異,以至于不少河南老鄉在戰時的傾向發生了大轉折:據說中原地區大約有5萬名中國軍人是被當地百姓繳械而失去戰斗力的,在國軍與日軍交戰時,日軍的傷員撤下來時有老鄉們搶著抬擔架,還有不少老鄉親自帶路,幫著日軍四處去追擊那些走投無路的國軍散兵,更有甚者,還出現了不少老百姓幫助日軍成建制的解除國軍武裝的例子。
歷史是復雜的,當大饑荒讓一切堅固的東西都變得輕飄飄時,記述這段歷史的《一九四二》反而厚重了起來,食指在詩中寫道:“我之所以堅定地相信未來,是我相信未來人們的眼睛——她有撥開歷史風塵的睫毛,她有看透歲月篇章的瞳孔。”當我們這些“未來人們的眼睛”注視著大銀幕上的《一九四二》時,我們的睫毛正在撥開歷史風塵,我們的瞳孔正在看透歲月篇章——對經歷了那場大災難的同胞來說,這是一場遲到但必須的告慰。
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