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歲學藝老字號
老家是蘇州吳江的褚宏生和兩千年前的范蠡是同鄉(xiāng),民國時期的詩人柳亞子也出生在那里。
褚宏生從小就性格好,又好看書,到16歲時,已經是秀逸聰慧少年郎了。父母看到兒子漸漸長大,就開始商量為他謀個一輩子的營生。“當時,我父母托了個熟識的朋友把我介紹到上海的一家裁縫鋪學習。他們認為學裁縫是在屋里,太陽曬不著,雨淋不著,自己有手藝混飯吃不是問題,而且學好了還可以開店子,很實惠。”
到上海之后,褚宏生投到“朱順興裁縫店”學手藝。“那個鋪子現在沒有了,以前就在北京西路485號。”老人回憶道,當時上海的裁縫店很多,但能趕上“朱順興”的卻沒有幾家。“朱順興”的老板叫朱林清,頭號大師傅叫朱漢章,在上海灘極負盛名,做旗袍是他的絕活。
在朱漢章所收的徒弟中,褚宏生是十分特殊的一個,師傅不讓他干活,只讓他抓緊時間練手藝。半年后,別的師兄弟都不做手工開始做縫紉了,但是師傅依然叫褚宏生做手工。“剛開始的時候我特別的不服氣,為什么別人都可以不做縫紉,而我就一定要繼續(xù)做。”幾年后,褚宏生才理解師傅的苦心,沒有十年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
杜月笙家的常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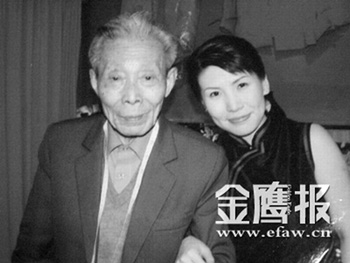 開始幫助師傅在店面接待客人、送衣服上門時,褚宏生不到20歲,還是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但這個少不更事的懵懂少年卻在不經意中進了杜月笙的家。那天是春節(jié)前夕,每戶人家都張燈結彩。忙到下午時,突然有輛黑色的轎車停在門口,說是要請裁縫上門量身,師傅便招呼褚宏生去。
開始幫助師傅在店面接待客人、送衣服上門時,褚宏生不到20歲,還是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但這個少不更事的懵懂少年卻在不經意中進了杜月笙的家。那天是春節(jié)前夕,每戶人家都張燈結彩。忙到下午時,突然有輛黑色的轎車停在門口,說是要請裁縫上門量身,師傅便招呼褚宏生去。
車子在一戶人家前停下了,那是褚宏生去過的最豪華的房子,高門廣第,奢華無比。進門后,他跟著仆人七繞八繞地進了主人的房間,看見一個中年人,穿著黑綢的開衫,身材有些瘦削,人長得有些嚴厲,但是說話時卻很和氣。“他要做幾件開衫和長袍,他的家人也要做很多衣服。那天忙到很晚才回家。”
后來褚宏生才知道,自己去的是堂堂青幫老大杜月笙的家,那個身材有些瘦削的中年人就是杜月笙。打那之后,杜月笙就成了這里的常客,去杜家也不是什么新鮮的事情了。褚宏生幫杜家做過很多衣服,直到解放前夕杜月笙逃往香港。前些年,杜月笙的孫子從國外回來時還特意到褚宏生的舊居探望過他。
胡蝶,記憶中最唯美的女子
褚宏生第一次見到胡蝶,是在她剛剛演完《歌女紅牡丹》的時候,那時的胡蝶紅極一時,剛剛當選電影皇后。
一個盛夏的傍晚,褚宏生去胡蝶家里為她量身。電影中的胡蝶總是濃妝艷抹,高貴逼人的,但褚宏生眼前的胡蝶卻穿著素凈的淡藍旗袍,沒有化妝,素面朝天。“她總是沖人笑,說話也很和藹,根本沒有明星架子。”褚宏生說。胡蝶對于旗袍的做工非常講究,也很注意旗袍的樣式,她十分喜歡復古式的花邊,或者稍微有點滾鑲。心情好的時候還會自己設計。
除了影后胡蝶,給褚宏生印象最深的女子,還有出身于書香世家的記者陳香梅。“一眼看去,她氣質大方,既具有大家閨秀的風范又有現代女性的堅強和穩(wěn)重,非同于一般的官太太。”褚宏生告訴記者,陳香梅對旗袍的料子是最為講究的,一定要選擇伸縮性好、手感柔軟的真絲料。“一般幫太太小姐們做衣服她們比較注重衣服的料子,這樣穿出來顯氣質。而幫交際花做的時候主要看式樣,顏色,料子就歸為其次了。”
王光美的廣告效應
新中國成立后,國內形勢起了很大的變化,“朱順興”等店面改為公私合營,經過改組成為“龍鳳服飾店”。在那個年代,來做旗袍的人不多。上個世紀60年代的時候,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出訪東南亞某國,臨行前到了趟上海,住在上海市政府禮堂,當時外事辦就介紹褚宏生為她做旗袍,從那之后,許多外使夫人便紛紛慕名而來。還有一些有出訪任務的地方領導和社會人士也來找褚宏生做旗袍。
演藝界和文化界的名人經常來找褚宏生。成龍的父親是他們店里的常客,整個店面的人都有龍爸爸的簽名。潘虹也很喜歡這里,她還把陳道明介紹來過。2000年,順子的媽媽黃愛蓮帶了來自7個國家的40多個學生在上海演出,就是找褚宏生定制的旗袍,《紐約時報》曾對此進行了報道,在紐約造成了不小的轟動。但褚宏生的旗袍在日本更受歡迎,松井菜惠子和今井美樹都是因為它們而經常往返于日本和上海之間。
退休后的褚宏生沒有回吳江老家,雖然膝下早已是兒孫成群,家里住的都是一幢幢的獨立小樓,可老人就是愿意一個人住在上海。因為上海人穿的旗袍里,存著他所有珍貴的記憶。
發(fā)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