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圈內朋友解釋,古董旗袍一般指清末和民國時期的旗袍。清末皇親國戚穿過,民國初年富家小姐穿過,愛國女學生穿過,十里洋場的佳麗名媛穿過……它是一個年代的符號,沉淀著時代的文化、歲月的痕跡,以獨特的面料、別致的款式、精湛的工藝記錄著那些時代愛美的女人們的故事。
古董旗袍不能穿,也沒人舍得穿。它只能用來欣賞,從幾百元一件到數十萬元一件,收藏的人忽然就多了。有的因為研究服飾文化的需要,有的因為作為設計和工藝的參考,有的因為純粹的個人愛好,還有更多人其實只是因為,愛旗袍永不褪色的優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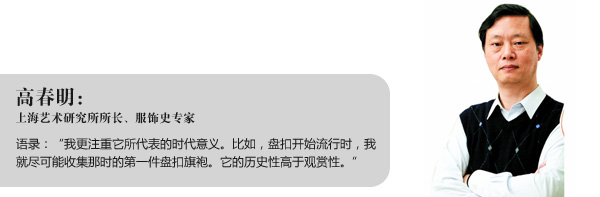
構筑百年旗袍譜系
他是目前中國服飾研究的權威,30多年來,收集了各個時期旗袍的代表作品,構筑了一個相對完善的“百年旗袍譜系”。他叫高春明。
最近高春明忙得昏天黑地,因為正在準備一場古今旗袍薈萃的特展,不僅會呈現如今上海灘老字號的精品旗袍,還將展示部分他30多年來收藏的古董旗袍。不像其他藏家,一般都很樂意展示自己的收藏,高春明并不太愿意將收藏的旗袍拿出來展覽,曾有美國、法國的相關單位向他邀展,他都婉言拒絕了。
他收來的旗袍存放在上海藝術研究所的服裝庫房,兩件一起裝在專業的密封袋里。這種從國外引入的密封袋由6種特殊材質構成,可防蟲防潮防氧化,5年之內不必另外護理。平時若是開一次袋子,藥性立馬揮發,好幾百塊就沒了。倒不是心疼這幾百塊錢,高春明說,主要是這些旗袍都是珍貴的文化資料,有些年代久遠的,質地脆弱,經不起折騰。比如胡蝶女士的一件真絲旗袍,薄如蟬翼,若是研究所里的男同志手腳稍重一點,就很可能抽絲。
這些旗袍對高春明來說都是無價的寶貝,因為是國家撥款、研究所收藏以進行服飾文化研究,高春明在收旗袍時可不敢亂花一分錢。他收旗袍最基礎的有三點,材質、紋樣和款式。
“我不是什么樣的旗袍都收,得有特色。要么材質特殊,要么工藝特殊,要么穿著人身份特殊。我更關注的還是一些有標志性變化的旗袍,最早使用拉鏈、最早使用襯肩、最早開叉……”
高春明學的美術專業,1976年,上海成立全國首家“中國服飾史研究室”,他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員,那時他不過20歲,一晃,在所里已有30余年,從當時的小研究員也坐到了如今所長的位置。

最初搜集服飾資料時,他發現,在浩瀚的古代服裝史里,旗袍是最有特點的女裝,是唯一一種被全國各民族女性,尤其是漢族女性接受的民族服裝,并曾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風靡全國。從此,高春明開始關注旗袍,每天流連于上海圖書館和徐家匯藏書樓。那時沒有復印機和電腦,高春明就將有用的資料一字字抄寫在筆記本上,不知不覺竟整理了十多本。
隨后,他根據資料到各地收集旗袍,“早期旗袍從北京、遼寧、黑龍江收,主要是清末的旗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海派旗袍風靡,就主要從上海及周邊地區收集,另外山東、陜西民間也收到一些特色的旗袍。”
為了更詳細地研究旗袍的發展變化,高春明閱讀了大量有關近代旗袍的期刊、報紙,同時將小說、電影、電視里女主角穿的旗袍也作為參考資料,他還遍訪滬上旗袍制作名家,對旗袍的文化淵源、審美情趣、工藝傳承進行系統整理,終于排出一個相對完善的百年旗袍譜系。“比如1925年流行什么旗袍,1930年1至3月出現什么標志性變化,土布旗袍大概何時出現等,有了這個譜系,我收藏旗袍就更加有的放矢。”
正因為出于研究的目的更多,高春明收藏的旗袍不是每一件都有視覺的美感。這一點,高春明坦然認同。“我更注重它所代表的時代意義。比如,盤扣開始流行時,我就盡可能收集那時的第一件盤扣旗袍。它的歷史性高于觀賞性。”

一件旗袍一個故事
隨著收藏的旗袍越來越多,高春明在民間收藏界的知名度越來越高,許多古董商人也經常請他去掌眼。他原本將此作為收藏旗袍的好機會,但事實卻是,只要他鑒定過的服飾,轉眼就在原價上加一個零,并注明“此物經高春明老師鑒定”。這樣一來,他的收藏成本和難度反而大大增加了。
一次,高春明聽說北京一位藏家收到一件藍色龍袍,他立即飛到北京,經鑒定,是真品。藏家要以10萬元轉賣給高春明,但高春明沒這么多錢,只好回上海打報告給單位,一級級報上去。一個月后,報告批下來,藏家早以15萬元的價格將龍袍賣給了韓國商人,韓國商人又以10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美國商人。他懊惱不已。“我是與古董商人賽跑啊。”高春明說。
又一次,高春明從朋友那得知有個沒落家族的后人要轉手一件旗袍,趕緊跑去。“那件旗袍應該誕生在1933年左右,無論面料、做工還是款式,都是當時的上上品。”更重要的是,它能填補百年旗袍譜系中的一個空缺。因沒能控制住自己激動的情緒,賣家當場把價錢翻了番。高春明沒下手,第二天再打電話過去,賣家竟又把價錢翻了幾番,一下就五千多了。高春明笑稱,收旗袍的過程就像做古玩生意,要有好眼力,要把握時機,還要當機立斷。
收旗袍的故事數不勝數,其中也有讓高春明感動的。那是對90多歲的老夫妻,通過各種渠道找到了他。老太太是袁世凱家族的后人,手上有件樣式精美的旗袍,是她媽媽親手縫制并穿過的。她每年都會取出來曬曬,撫摩面料,似乎還能感受到媽媽的體溫。她說,這件老衣服與其留給兒女壓箱底發霉,還不如找個更好的歸宿。交到高春明手上,他們最放心。
在高春明看來,每件旗袍都在訴說故事。收藏它們,不僅是在讀那些歷史、工藝、文化的故事,還讀著穿著旗袍的那個人的故事。
為了讓更多中國人了解旗袍的故事,2006年,高春明借著旗袍成功申報上海市級非遺的機會,策劃了一場“百年旗袍展”,由他和幾位設計師一起復原設計了近百款百年來各個時期不同款式的旗袍。那是高春明收藏旗袍30余年來唯一舉辦的一次旗袍展,“說白了,我辦展覽也好,推廣也好,完全是為弘揚民族文化,因為我不賣一件旗袍,我是花錢的,不是掙錢的,為了旗袍而花錢。但是我想讓更多企業做好,讓更多喜歡旗袍的女性也來花錢,從而讓旗袍文化發揚光大。”
收藏和研究旗袍這么些年,高春明認為,旗袍之所以存在生命力就因為它在不斷創新和變化,“適當改良是應該的,老一個款式,它就真該進古董店了。”但旗袍也需保持其標志性的元素:立領、連身、開叉。對于有些設計師對傳統旗袍進行夸張設計和改變,高春明搖搖頭,“我覺得那玩的是概念,未必有生命力,還不如叫時裝比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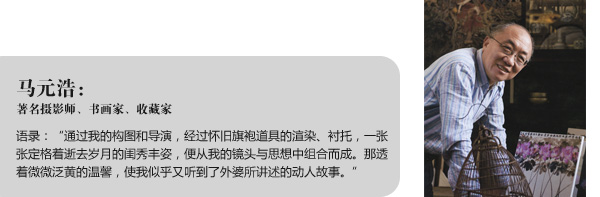
定格逝去的歲月
6月,上海新天地壹號會所,另一場小小的個展靜悄悄地拉開了帷幕。看真實的旗袍,看鏡頭下的旗袍,看畫里的旗袍……恍惚間,一場“旗袍麗人行”,好似帶人走進一段旗袍冷艷迷離的歲月。
展覽者叫馬元浩,他是攝影家,曾出版過多部攝影集,舉辦過很多攝影展;他也是收藏家,收藏了近300件古董旗袍。在馬元浩眼里,旗袍是中國女人的歷史證物,他熱愛旗袍,收藏旗袍,如珍視初戀一般將旗袍占為己有。
會所里展出的實物旗袍數量并不太多,有滿清旗人穿的旗袍,也有民國闊小姐穿的旗袍。有的旗袍鑲滾著繁復的寬窄邊,有的旗袍繡著精致的花卉或祥云,還有的旗袍以生絲織成,時隔幾十年都未褪色,還能觸摸到幾分硬挺的質感。
“旗袍里有很多學問,在設計與穿著上也有很多規矩。”馬元浩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階層穿的旗袍都有很大不同。“我收藏這些旗袍,就是想保留下這些民族的精粹的東西,因為時間越久,這些美好的東西就會流失,后來的人就沒機會看到曾有過這么美的服裝被前人穿過。”

馬元浩的旗袍收藏源于自己對拍懷舊人物照的喜愛。上世紀八十年代,馬元浩熱忱于拍攝電影明星,陳沖、劉曉慶、張瑜、龔雪等都是他鏡頭下的常客,一年要出版她們大量的月歷和年歷。月歷上的明星經常身著旗袍,婀娜多姿,仿佛重現上海舊時歲月,馬元浩由此愛上了拍攝懷舊人物照,并開設了專拍懷舊照的影樓“源源坊”。
為了讓服飾更加豐富,馬元浩開始有意識地收集上海大戶人家里流落出來的旗袍。一有新旗袍到手,他就拿到相熟的旗袍師傅那里,先仿制出來。“當然是仿個大概樣子,有些古董旗袍工藝繁復、繡工精湛,要想仿得一模一樣是不太可能的事。”然后,他將古董真品噴上酒精,裝進樟木箱保存起來。慢慢地,他的工作室里已有五六個裝滿古董旗袍的大箱子。

如果說最初開懷舊影樓的動機是因為市場需求,但隨著收藏的旗袍越來越多,了解得越來越多,天生愛創作的馬元浩又有了想法,他要把每件旗袍都拍出那時那代的風韻,以攝影的方式將旗袍文化表現出來,保存下來。“通過我的構圖和導演,經過懷舊旗袍道具的渲染、襯托,一張張定格著逝去歲月的閨秀豐姿,便從我的鏡頭與思想中組合而成。那透著微微泛黃的溫馨,使我似乎又聽到了外婆所講述的動人故事。”
因為這種對旗袍文化別具一格的呈現方式,他拍的美女旗袍照曾被制作成一套名為《海上遺韻》的明信片發行,上海畫報出版社更將那些照片集結起來,編成《飄逝的羅裙》一書,作為馬元浩的藏品集,也作為他的攝影作品集,記錄下中國女子服飾的發展變化。
如今,因精力有限,68歲的馬元浩已經關閉了上海的影樓,但他依然還在拍旗袍女人的照片。中國女人穿旗袍最好看,馬元浩堅持這樣認為。“你看看,那些穿上我旗袍的女人們在照片里真的比她們平時美得多,更像中國女人。”
發表評論